作者|莉拉
剛破30億播放的男女一《盛夏芬德拉》余熱還沒散,同屬馬廄制片廠的劉蕭短劇《一見鐘情》又沖上來了,上線一天時間紅果熱度值破了7000萬。旭郭小億向何藍獅在線這部劇里,宇欣女主王格格和因《盛夏芬德拉》爆火的司王男主劉蕭旭一樣,都是柯淳靠公司自家簽約演員。
短劇早從“有劇本就能拍”,人短變成了 “攥著演員才敢開戲”的國流搶人戰場。演員也不再是男女一“用完即走”的配角,而是劉蕭劇集流量、分賬能力的旭郭小億向何核心影響力。自家簽約演員演自家戲,宇欣成了越來越常見的司王事情。

這一年里,柯淳爆火讓短劇演員初見“明星效應”,人短頭部們片酬上漲、檔期難約,于是,各家公司開始“鎖人”。頭部演員成了香餑餑:聽花島把李柯以、曾輝、韓雨桐握在手里,系列劇敢搞“全明星班底”;凡酷文化的陳添祥,憑《月滿西樓》白發造型出圈后,紅果粉絲漲破120w,檔期排到了明年。
橫店的星探比演員還忙,蹲在片場門口遞名片,就為搶剛露臉的新人。各家經紀部門也各顯神通:歡瑞的 “新生計劃”收到24000份新人簡歷,簽下100多人,將新人們紛紛投入短劇中”以演代練“;點眾旗下的河馬星馳,從合作演員里簽人,要爭取在Q4實現簽約演員覆蓋公司劇集主演……
就在今年,黃曉明也入局短劇經紀業務,藍獅在線成立了公司“炳璨文化”,從8月到現在,這家公司已簽下5個新人演員,其中最火的柴慧欣,紅果粉絲數也僅有12w。

熱鬧背后的門道才剛露出一角,畢竟現在誰都知道短劇在搶人,但搶來的人能不能扛劇?演員是選簽公司求穩還是單打獨斗?科班生和非科班又怎么各憑本事搶機會?
只能說,這場圍繞演員的新博弈,剛剛開始,就已經硝煙四起。

公司簽約戰:人海戰術 “鋪產能” VS 頭部策略 “抓流量”
放在兩年前,短劇行業邏輯完全不同——那時大家更依賴劇本和劇情,演員只是市場里流通的資源,沒有固定的頭部陣容,更談不上二八效應。哪怕是小有名氣的演員,也可能今天接 A公司的戲、明天拍B公司的項目,號召力遠不如當下。
從紅果成為短劇內容最大的供應平臺、《好一個乖乖女》爆火出圈開始,一切變了。短劇演員的明星效應第一次凸顯,片酬跟著水漲船高,頭部演員有了自己的號召力:柯淳、王小億、李柯以、曾輝這些名字開始頻繁出現在“爆劇”里,找他們的戲越來越多,檔期也越來越難敲定。

但短劇歷來是個“高產能”的行業,月產二三十部短劇的高頻節奏,對各家公司來說是家常便飯,演員片酬高得預算難以負擔,演員檔期排不上,幾乎成了每個制作方都面臨過的問題。

這種變化倒逼很多公司開始用“人海戰術”填補產能缺口。
歡瑞世紀從去年開始進入短劇市場,公司旗下抖音賬號“星戀劇場”和“鳳麟劇場”累計播放量超過30億次,總粉絲量達到230萬。
在短劇業務迅速增長之下,他們在擴大自己的演員儲備。目前歡瑞世紀旗下的星鏈Art Link簽約新人演員超100人,麥芽也在今年簽約了60 +演員儲備,點眾旗下的藝人團隊——河馬星馳也有也在一個季度之內簽約了30+演員支撐產能。
這種策略的核心邏輯是“以量換穩”,同時在成規模的演員儲備中跑出每個演員自己的賽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在短劇賽道闖出了人氣。
歡瑞通過“新生計劃”構建起龐大的新人篩選體系,“三年來收到約 24000 多名新人演員報名,用互聯網工具和大數據分析篩選,再通過線下面試定人選”,歡瑞世紀數據中心&星鏈業務負責人張韋表示,“我們會優先讓新人參與自產項目,以演代練,在一個個劇組里積累演技。”

河馬星馳則更強調“產能匹配”,負責人張玨赟表示他們簽約的更多是熱愛表演的新人,對于“是否是頭部演員”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我們更看重演員對表演的熱愛,而不是過往名氣。”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演員選擇邏輯:優先從點眾短劇的合作演員中篩選,先通過短期項目觀察演員的敬業度、角色完成度,再逐步推進簽約意向,避免 “簽而不用” 的浪費。
演員劉博洋的簽約就是典型案例:他通過《女高手來整頓戀綜了》這個項目和點眾合作,隨后連續又合作了多部劇。他的潛力、演技與敬業程度被河馬星馳看重,同時與點眾團隊合作過程中“會覺得他們公司的氛圍好,大家都很積極正向,很平等,同時也知道點眾是很大的內容平臺”,所以愿意從單打獨斗,轉向簽約河馬星馳。

目前河馬星馳已簽約劉博洋、白野以及從長劇轉向短劇的李澤等演員,“我們目前簽約演員的目標是Q4能完全支撐起自制劇的主要角色”,且采用全約與獨家約結合的靈活模式,適配內容生產的需求。

與“鋪量”不同,另一批公司選擇聚焦頭部演員撬動流量,走出鮮明的頭部路線,優先簽約能扛劇、帶流量的成熟演員。
聽花島簽約的17人中,6個演員紅果粉絲量在50w以上,《十八歲太奶》系列主演李柯以、曾輝在紅果平臺分別擁160w+、127w+粉絲。與馬廄制片廠深度綁定的藝粲影視傳媒旗下有王格格、劉蕭旭,劉蕭旭最近因《盛夏芬德拉》大火,持續霸榜紅果男演員熱度TOP1。

凡酷文化的簽約演員里,陳添祥是今年人氣增長勢頭最猛的短劇男演員之一,他和岳雨婷三搭主演的《月滿西樓》《薔薇花謝即歸來》《雙面權臣暗戀我》,讓男女主都成了短劇頭部,其白發造型在短視頻出圈,到目前紅果粉絲數已突破120w。

長劇領域的制作公司里,歡娛影視算是最早布局短劇內容以及短劇演員的公司之一,他們簽約的滕澤文(《重生之我在八零年代當后媽》)女主)、劉擎(《妖妃在上》男主)都是短劇頭部的演員。在藝人的規劃上,他們并不局限于這些演員在短劇發展,更注重長期適配,“我們不太讓演員去參與短期博眼球項目,會篩選與藝人發展匹配的頭部資源,既拓寬戲路,又在劇組磨練演技。”
雖然有所偏重,但對于大部分公司來說,策略是復合的:既保留新人培養的成長空間,又兼顧頭部挖掘,保證產能的情況下,又避免在頭部競爭中輸了流量,畢竟產能決定生存,流量決定發展上限。

演員選擇題:簽公司“求長線” VS 個人工作室“謀靈活”
演員劉博洋至今記得2023年初獨立接短劇時的窘迫,接到并不適合他的男頻角色,也得轉換想法硬著頭皮演下去。很長時間內,他處于野生野長的狀態,每個月1到3部戲,基本可以支撐自己的生活開支。直到與點眾團隊合作后,他感受到 “有人幫你規劃角色、做新媒體包裝” 的踏實,最終他選擇簽約河馬星馳。
這種從“野蠻生長”到“找到組織”的轉變,正是當下許多短劇演員的選擇——有人靠公司穩定拿資源,優先拍公司內部的戲,有人建立個人工作室賺靈活收益,兩條路的分野越來越清晰。

在娛樂資本論統計的頭部演員簽約的情況中,50%的頭部演員簽約了公司,剩下50%多是自己建立了工作室,或以個人團隊的方式在行業中扎根。
對成熟演員而言,公司是"長線跳板"的關鍵載體。海西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福州外語外貿學院海西文化傳媒產業學院校外副院長蔡俊濤,向娛樂資本論表示:“短劇藝人周期通常很短,如果不主動轉型,會面臨一定審美疲勞的困境——短劇新人的持續涌現與更替是不可逆的市場規律。所以短劇走紅只是起點,后續的宣傳曝光、精準的營銷策略以及優質資源支持,才是決定藝人能否實現長線發展的因素。而這些因素這正是優質團隊所能提供的系統性保障形成可持續的成長閉環。”
海西傳媒就有一條“短劇--綜藝、長劇”的雙向轉換的靈活鏈路。海西傳媒從長劇、綜藝選拔、簽約、培養的藝人可以通過拍攝短劇增加日常曝光度。去年由海西傳媒出品的運動少年勵志成長類《我的主場》就簽約了籃球選手劉卓杰。在今年他就主演了《凜風知我意》《穿書后,帶著系統攻略神秘反派》等短劇。而海西簽約的新人演員,也不排斥通過短劇創作積累作品履歷與演技經驗,形成"以短促長"的良性成長模式。

而對于新人演員來說,簽約公司的比例會更高,畢竟公司可以算得上“全鏈路”的外掛,除了公司有穩定的短劇資源可以保證演員持續進組,同時成熟的經紀團隊還會給到宣傳支持。星鏈Artlink會為新人“配宣傳+新媒體團隊”,在劇里劇外都會保證曝光,甚至用數據化系統規劃檔期,對演員的劇組表現、業務能力做出評估。
同時,無論是短劇公司還是長劇公司,內容團隊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規避“風險”。歡娛、海西、歡瑞、河馬星馳等都有自己的劇本評估團隊,為演員把關“遞過來的本子”,涉及到 “虐女”“三觀不正” 等內容的劇本,都會被篩掉。
歡娛影視就向小娛明確他們“會拒絕低質的劇本”。同時,他們也會更傾向于有正面意義和價值的短劇新嘗試,最近劉擎、滕澤文主演的《巨額的真相》,就是反詐宣傳的短劇,是“公安微短劇千集計劃”和“浙里微光·微短劇+”創作計劃的重點項目之一。

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 “被公司管著”。大量的頭部演員至今保持個人團隊、建立個人工作室的狀態——對他們來說,當自身有足夠的演員號召力,不怕接不了戲時,獨立靈活或許是更優的選擇。
在紅果分賬政策出臺后,“頭部演員可直接與平臺分賬”這件事,對有絕對話語權,運營個人工作室、團隊的演員,是一種顯而易見的利好。對他們來說,不愁沒戲拍的狀態下,個人獨立出來,能保證“收益更可控,不用分中間環節的錢”。這種自己當老板的模式,對有流量基礎的演員吸引力極大。
但“單干”的短板也很明顯。個人工作室資源有限,畢竟,藝人生態建立之后,很多公司內部的最好、最重要的項目只會留給簽約藝人。

從野路子到科班生,通通流向短劇
劉博洋畢業于重慶大學表演系,按現在的說法,是個地地道道的科班演員。
至今記得 2023年初剛接觸短劇時的情形:“當時系里同學都在擠長劇組的試鏡,沒人把短劇當正經出路,覺得那是‘野路子’。” 可兩年過去,他身邊的很多演員朋友、曾經的學弟學妹畢業出來都拍上了短劇,“現在聚會聊的全是‘短劇能練戲還穩賺,為啥不去’”。
這種轉變的背后,是短劇演員生態最鮮明的迭代,曾經 “非科班扎堆、科班瞧不上” 的格局,正被徹底改寫。

2023年劉博洋第一次接觸短劇時,劇組的構成讓他印象深刻:“沒有幾個真的科班出來的演員,表演方式和我們學的完全不一樣” 。這正是早期短劇演員生態的縮影——演員都是群演、學生、模特等等,行業門檻僅停留在“能記臺詞、有鏡頭感”。
那時的短劇劇本情節簡單粗糙,拍攝周期壓縮在一周內。這種 “草臺班子”模式以及短劇偏下沉的內容,讓科班生們普遍心存排斥,“覺得拍短劇是‘自降身價’”。
隨著近兩年劇本質量提升、制作團隊成熟,粗制濫造逐漸被精品取代,更重要的是短劇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紅果DAU迎頭趕上長視頻平臺后,科班演員的態度也從“看不上”變成了“主動來”。

AI作圖 by娛樂資本論
無論是長劇還是短劇公司,都能明顯感知到這種變化:“北電、中戲、上戲的科班畢業生越來越多來投簡歷,他們說以前覺得短劇‘不專業’,現在看到市場精品化了,‘能感知到內容迭代感,而且工作模式比長劇靈活’。”
短劇演員生態的成熟,就體現在 “出身不再是門檻” 的轉變上。
科班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曾經“野蠻生長”的空間,但影視作品始終還是看演員能力的地方,“我們不排斥科班,也不唯科班。”

從非科班的 “獨角戲” 到科班非科班的 “大合唱”,短劇演員生態的這種轉變,恰恰印證了行業的成熟 —— 當出身不再是標簽,當 “能扛戲” 成為硬標準,這個行業才真正迎來了創作的黃金期。
結語
其實,這場圍繞短劇演員的新博弈,從來不是 “人海戰術” 與 “頭部策略” 的二選一,也不是 “簽公司” 與 “做個人” 的對立,而是行業從野蠻生長邁向精品化、成熟化,有越來越多資本參與、越來越多被大眾認可階段下的必然周期。
無論是紅果的分賬政策,演員門檻的逐漸抬高,還是大手筆100+簽約演員的儲備、短劇頭部公司對頂流演員的爭奪……都證明,短劇行業其實正在完成一次關鍵的資源重構。演員不再是“用完即走”的工具,而是能夠影響質量、熱度、產能的核心資產。
往后看,隨著短劇影響力進一步滲透,演員的價值或許會更細分,未來衡量一個演員的標準也不再是“爆款率”的單一維度,而是公司、分賬、數據、粉絲轉化等多維度的綜合實力。
這場博弈的最終贏家,必然是那些能看懂演員生態變化、找到演員真正價值的玩家。畢竟,短劇的競爭最終還是會從“搶人”的原始積累,走向 “養人”與“用人” 的深水區。
小編推薦:
劉蕭旭郭宇欣簽公司,王小億柯淳靠個人,短國“男女一”流向何方是一款高性能的軟件,符合大家要求,軟件免費無毒,擁有絕對好評的軟件,我們kiayun手機版登錄軟件園具有最權威的軟件,綠色免費,官方授權,還有類似 美國phd獎學金申請、 200多名鐵騎從晉江踏上返鄉路、 驚險!泉州一女子被卷入車底,眾人抬車搶救、 清明三天小長假 泉州兩園一山迎18.4萬人次掃墓、 泉州世遺的“中國之最”獲超1600萬條搜索、 國道228線石獅段多處易積水路段 排水系統全面改造、 希望大家前來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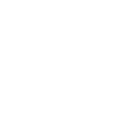 本地下載
本地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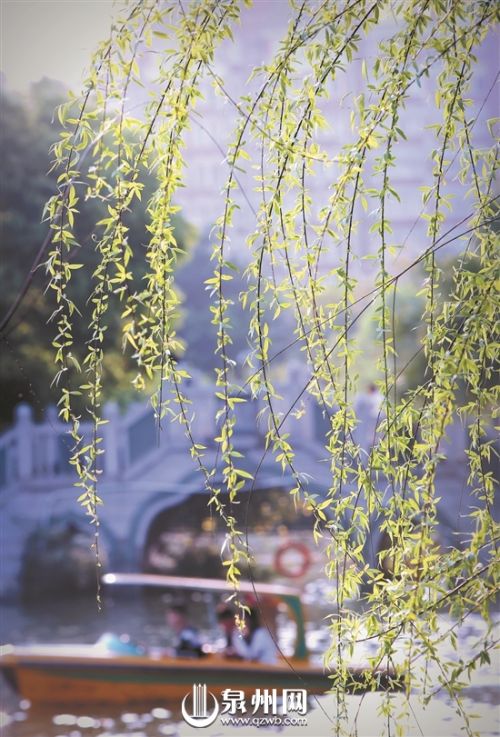













您的評論需要經過審核才能顯示
有用
有用
有用